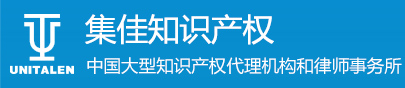-
文/北京市集佳律師事務所 張秋林
現實中客觀存在侵權證據妨礙,并因此需要排除侵權證據妨礙。可從作為一般法的司法解釋中找到適用排除侵權證據妨礙的相關法律依據。同時,排除侵權證據妨礙已經在司法實踐得到了相對廣泛適用。根據《加強產權司法保護意見》,期待排除侵權證據妨礙制度能在司法實踐中得到更廣泛應用。
關鍵詞:專利;侵權;證據妨礙;侵權證據妨礙
2016年12月8日北京知識產權法院作出了該院自建院以來的最高判賠額5000萬元,其中85.8萬元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下文簡稱“《專利解釋二》”)第二十七條證據妨礙相關規定作出。在此約20天前北京知識產權法院作出了1000萬元的次高判賠額。該案涉及商標侵權,1000萬元賠償額全部根據《商標法》第六十三條第二款[2]證據妨礙相關規定作出。
根據《專利解釋二》和《商標法》相關規定以及上述兩個案例,證據妨礙似乎只適用于侵權賠償額的確定。這在相關文獻期刊中也有一定體現。例如,劉曉博士認為:“在專利案件中,《專利解釋二》屬于特別規定,適用順位先于同為司法解釋的《證據規定》、《民訴解釋》等一般規定,因此,專利案件應適用《專利解釋二》第二十七條。[3]”又例如,宋建寶法官呼吁:既然已經將舉證妨礙制度的設計理念從只重公法效果轉換到了公私法效果并重,那么在舉證妨礙制度的適用范圍上,是否也可以從確定損害賠償額擴大到認定專利侵權事實?[4]”
證明妨礙又稱舉證妨礙、證明受阻,是指不負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故意或過失以作為或不作為的方式,使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不能提出證據,進而使待證事實無證據可資證明并真偽不明。
在專利侵權案件中,專利權人既需要提供侵權證據,也需要提供賠償證據。相應地,被控侵權人既可能在侵權判定中妨礙舉證,也可能在賠償確定中妨礙舉證。因此,既需要在賠償確定中排除證據妨礙,也需要在此之前于侵權判定中排除證據妨礙。
筆者下文將從加強產權司法保護文件精神、侵權證據妨礙存在的客觀性、相關法律規定、相關典型案例及其適用條件五個方面對專利侵權事實認定中的侵權證據妨礙進行具體論述。
一、加強產權司法保護文件精神
201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其中第九條提出了加大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懲治力度,提高知識產權侵權法定賠償上限,探索建立對專利權、著作權等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對情節嚴重的惡意侵權行為實施懲罰性賠償,并由侵權人承擔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提高知識產權侵權成本。根據上述意見第九條,2016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切實加強產權司法保護的意見》(下文簡稱“《加強產權司法保護意見》”),其中第十一條提出了適時發布司法解釋和指導性案例,通過排除侵權證據妨礙、合理分配當事人的舉證責任等途徑,依法推進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適用。該意見第十一條規定明確提出了“侵權證據妨礙”這一概念。所述概念既反映了現實中存在嚴重的侵權證據妨礙,也表明了今后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工作重心之一就在于排除業已存在的嚴重侵權證據妨礙。
二、侵權證據妨礙存在的客觀性
專利權利要求分為產品權利要求,例如物品、物質、材料、工具、裝置、設備等,和方法權利要求,例如制造方法、使用方法、通訊方法、處理方法以及將產品用于特定用途的方法等。
就產品權利要求而言,為了證明被控侵權人存在侵權行為,通常是從市場公開渠道公證購買獲得被控侵權產品,然后將其與專利權人據以主張權利的權利要求進行比對,判斷控侵權產品是否落入權利要求保護范圍。然而,這并不適用于所有被控侵權產品,例如化學組合物或者為被控侵權人控制的產品等,其中后者例如包括僅在工業生產過程中使用的催化劑產品和主要由服務器構成的系統平臺等。即便是專利權人合法地獲取了作為被控侵權產品的化學組合物,其仍可能無法通過化學測試方法準確獲知該化學組合物的組成,多種組分的復雜組合物更是如此。在工業生產過程中使用的催化劑產品一方面可能來自于被控侵權人的自給自足,另一方面可能來自于特定關聯方的直供特供。在上述兩種情況下,專利權人根本就無法獲得所述催化劑產品,更不用說通過反向工程分析獲得其化學組成。主要由服務器構成的系統平臺則更是完全為被控侵權人所控制。當被控侵權產品是這些產品時,為了證明被控侵權人存在侵權行為,專利權人將不得不依賴于被控侵權人主動或被動提供被控侵權產品及其技術信息,或者依賴于法院調查取證、勘驗或證據保全。在第一種情況下,被控侵權人完全有可能提供虛假的被控侵權產品以假亂真。在第二種情況下,被控侵權人輕則不積極配合法院工作,重則強烈或甚至暴力阻擾法院調查取證、勘驗或證據保全。由此可見,在證明被控侵權人實施侵犯產品權利要求行為的過程,確實存在舉證困難,這種困難一方面可能來自于客觀上難以接近或獲得被控侵權產品,一方面可能來自于被控侵權人的弄虛作假和阻擾等妨礙。
與產品權利要求相比,專利權人更加難以證明被控侵權方法落入了方法權利要求保護范圍,因為被控侵權方法通常由被控侵權人在封閉空間中實施,并因此完全為其所控制。為了破解這一舉證難局,早在2000年《專利法》第五十七條第二款就對此進行了如下規定:專利侵權糾紛涉及新產品制造方法的發明專利的,制造同樣產品的單位或者個人應當提供其產品制造方法不同于專利方法的證明。2008年《專利法》完全保留了上述規定[5]。《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本文簡稱“《證據規定》”)中也存在類似規定[6]。這些規定實際上將侵權行為的證明責任從專利權人倒置給了被控侵權人,從專利權人證明被控侵權方法與方法權利要求相同變為被控侵權人證明被控侵權方法與方法權利要求不同。然而,上述規定只適用于“新”產品,而不適用于非新產品。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309號對立法者之所以如此制度安排的原因進行了具體分析[7]。就涉及制造非新產品的方法權利要求,仍存在上文就產品權利要求所述相同問題,即專利權人不得不依賴于被控侵權人提供被控侵權方法的技術信息,但被控侵權人很可能弄虛作假,或者依賴于法院調查取證、勘驗或證據保全,但被控侵權人極可能消極不配合,或者強烈或暴力阻擾法院工作。
由以上論述可知,據以主張權利的權利要求無論是產品權利要求,還是方法權利要求,在專利權人證明存在侵權行為的過程中,均很大程度上或客觀存在由被控侵權人的弄虛作假、消極不配合和阻擾等行為導致的證據妨礙。
三、排除證據妨礙的相關法律規定
《專利解釋二》第二十七條規定:在權利人已經提供侵權人所獲利益的初步證據,而與專利侵權行為相關的賬簿、資料主要由侵權人掌握的情況下,人民法院可以責令侵權人提供該賬簿、資料;侵權人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或者提供虛假的賬簿、資料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權利人的主張和提供的證據認定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專利法修訂草案(送審稿)[7]第六十八條存在類似規定:人民法院認定侵犯專利權行為成立后,為確定賠償數額,在權利人已經盡力舉證,而與侵權行為相關的賬簿、資料主要由侵權人掌握的情況下,可以責令侵權人提供與侵權行為相關的賬簿、資料;侵權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虛假的賬簿、資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參考權利人的主張和提供的證據判定賠償數額。
根據上述兩個規定,被控侵權人造成的證據妨礙包括(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或提供虛假的賬簿資料,法院排除所述證據妨礙的目的僅在于如何判定侵權賠償數額。這也就是說,上述兩個規定并沒有明確禁止在侵權認定中排除證據妨礙。因此,能否在專利侵權認定中排除證據妨礙則主要取決于在一般法中是否存在相應法律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第三十條規定:有證據證明持有證據的一方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的內容不利于證據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證據規定》第七十五條基本完全沿襲了上述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本文簡稱“《民訴解釋》”)第一百一十二條規定:書證在對方當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擔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可以在舉證期限屆滿前書面申請人民法院責令對方當事人提交。申請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應當責令對方當事人提交,因提交書證所產生的費用,由申請人負擔。對方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認定申請人所主張的書證內容為真實。
作為一般法的上述三個規定并沒有明確其具體適用范圍。相應地,應認為所述三個規定既可適用于認定侵權事實,也可適用于確定賠償數額。因此,根據上述三個規定,完全可以在專利侵權認定中排除證據妨礙。下文將從實踐角度考察上述排除證據妨礙相關規定在司法審判中的實際應用。
四、排除侵權證據妨礙的典型案例
1.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09)浙知終字第187號民事判決書(2010年中國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50件典型案例)
(1)侵權證據妨礙行為
一審法院前往被控侵權人進行證據保全,確認在該公司草甘膦尾氣回收氯甲烷的生產現場中包含了“水洗泵”等相關設備裝置,并以拍照、拍攝等形式進行證據保全,但被控侵權人拒絕提供相應圖紙等資料并進行阻攔,致使證據保全無法繼續進行。在第二次證據保全中,被控侵權人向法院提供了一套“尾氣處理生產工藝流程圖”,但一審法院發現涉案生產現場明顯發生了改變。
(2)排除侵權證據妨礙行為
一審法院向杭州市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建德市公安局調取了被控侵權人“氯甲烷回收生產工藝流程圖”,從杭州市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調取了被控侵權人備案的安全預評價報告以及從浙江省環境保護科學設計研究院調取了被控侵權人年產6000噸草甘膦技改項目環評報告中的“氯甲烷回收車間流程”。將被控侵權人的“氯甲烷回收生產工藝流程圖”和“氯甲烷回收車間流程”中顯示的草甘膦尾氣回收氯甲烷生產工藝與專利權人的涉案專利方法相比對,兩者無論是設備配置、操作步驟,還是三級處理的工藝流程均相同,落入了涉案專利的保護范圍。
2. 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39號民事裁定書
(1)侵權證據妨礙行為
一審法院委托鑒定時,被控侵權人之一先是表示被訴侵權設備已經停產,不再使用;后又以設備過大需要拆解、停產時間較長等為由不同意拆解。在專利權人同意就被控侵權人停產造成的損失提供擔保后,被控侵權人無正當理由仍然拒絕鑒定。被控侵權人之二作為生產商,以設備是早年生產等為由表示無法提供圖紙。
(2)排除侵權證據妨礙行為
專利權人在一審中提供了相關公證書、法院證據保全照片、技術專家侵權對比分析意見等證據材料,已經初步證明侵權事實成立,因此推定專利權人的訴訟主張成立。
3. 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309號民事裁定書
(1)侵權證據妨礙行為 第一次證據保全中,被控侵權人稱其負責人不在,阻止一審法院進入生產現場;第二次證據保全中,該公司將一審法院帶至棉漿粕生產現場而非專利權人提供的視頻資料所顯示的生產現場。
(2)排除侵權證據妨礙行為
一審中,專利權人提供了“XXXX公司棉漿粕出門證”、“XXXX公司漿粕質量檢驗單”等一系列證據證明被訴侵權人生產銷售了涉案產品,并且通過產品檢驗等方式證明了涉案產品是與涉案專利方法生產的產品相同的粘膠木漿粕。對于涉案產品的制造方法,專利權人提供了其所拍攝到的被訴侵權人的生產車間、相關機器設備以及原材料木漿板投放過程的視頻資料。
綜合考慮雙方當事人已經完成的舉證情況、距離證據的遠近等因素,將證明涉案產品制造方法的舉證責任分配給被訴侵權人承擔。被訴侵權人應當并且也完全有能力提供證據證明涉案產品制造方法不同于專利方法,但在法院釋明后,其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涉案產品制造方法證據,據此認定其生產涉案粘膠木漿粕產品的制造方法落入涉案專利權保護范圍,專利權人的侵權指控成立。
4. 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提字第158號民事判決書(2010年中國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50件典型案例)
(1)侵權證據妨礙行為
被控侵權人拒不提供其產品批生產記錄及GMP申報材料等記載涉案藥品詳細生產過程的資料。
(2)是否需要排除侵權證據妨礙
一二審法院均認定被控侵權人生產被訴侵權產品所使用的技術方案即為專利權人申請調取的國家藥監局藥品批準文號“國藥準字Z20050221”藥品注冊批件的YBZ08242005標準(試行)及晨牌藥業公司報送的“獨一味軟膠囊”生產工藝的研究資料所載明的技術方案,可以以該技術方案的特征與涉案專利權利要求1記載的相應技術特征進行比較。從該技術方案的內容看,對于獨一味清膏干燥后研磨細度的要求,只有“研成細粉備用”的技術特征,沒有“過200目篩”的技術特征,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2000年版,一部)的規定,“研成細粉”是指過80目篩的細粉,被控侵權人提交的批生產記錄也進一步佐證該生產工藝在過80目篩后并無過200目篩的工藝步驟。可見該項工藝是完整的。原審判決以調取的生產工藝不完整為由,根據《證據規定》第七十五條的規定,簡單推定“研成細粉”與“粉碎成細粉,過200目篩”等同,顯然不妥。人民法院認定案件事實,應當首先根據現有證據進行。就本案來說,已經有一審法院調取的被訴侵權產品的生產工藝方法、被控侵權人提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2000年版,一部)以及專利權人提交的涉案專利權利要求書和說明書等現有證據,根據這些證據記載的內容,完全可以認定調取的生產工藝中記載的“研成細粉備用”,是指過80目篩的細粉,而不是過200目篩的細粉,其工藝是完整旳,根本不需要再根據《證據規定》第七十五條的規定進行推定。退一步說,如果認為被控侵權人沒有按照藥品標準載明的生產工藝生產被訴侵權產品,也應當根據民事訴訟法和專利法有關證據保全的規定,依法進行證據保全,譬如現場勘驗、査封扣押生產記錄等,而不是簡單地根據《證據規定》第七十五條的規定進行推定。原審判決一方面把從國家藥監局調取的生產工藝認定為被訴侵權產品所使用的技術方案,但另一方面又對該技術方案中記載的與涉案專利權利要求1不同的技術特征不予認定,進行所謂的推定,似存在雙重標準,難以令人信服。
五、適用排除侵權證據妨礙的條件
參考《專利解釋二》和專利法修訂草案(送審稿)排除賠償證據妨礙相關規定,結合上述正反兩方面案例,可以看出適用排除侵權證據妨礙通常需要滿足如下條件:1. 專利權人已盡最大可能收集獲取證據,并提供了侵權初步證據;2. 法院已盡可能收集獲取證據,例如通過調查取證、勘驗、證據保全和司法鑒定;3. 被控侵權人存在妨礙法院工作的行為,例如弄虛作假、阻擾,且具有主觀惡意。
綜上所述,現實中客觀存在侵權證據妨礙,并因此需要排除侵權證據妨礙。可從作為一般法的司法解釋中找到適用排除侵權證據妨礙的相關法律依據。同時,排除侵權證據妨礙已經在司法實踐得到了相對廣泛適用。根據《加強產權司法保護意見》,期待排除侵權證據妨礙制度能在司法實踐中得到更廣泛應用,進而對被控侵權人施以處罰,從而加強專利司法保護,鼓勵發明創造,促進科技進步。
注釋:
[1] 《商標法》第六十三條第二款 人民法院為確定賠償數額,在權利人已經盡力舉證,而與侵權行為相關的賬簿、資料主要由侵權人掌握的情況下,可以責令侵權人提供與侵權行為相關的賬簿、資料;侵權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虛假的賬簿、資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參考權利人的主張和提供的證據判定賠償數額。
[2] 劉曉;知識產權損害賠償中證明妨礙規則的成本收益分析;證據科學;2016年05期,第567-575頁。
[3] 宋建寶;舉證妨礙制度在專利侵權案件中的具體適用; 人民司法;2015年01期,第84-86頁。
[4] 《專利法》第六十一條 專利侵權糾紛涉及新產品制造方法的發明專利的,制造同樣產品的單位或者個人應當提供其產品制造方法不同于專利方法的證明。
[5] 《證據規定》第四條 下列侵權訴訟,按照以下規定承擔舉證責任:(一)因新產品制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由制造同樣產品的單位或者個人對其產品制造方法不同于專利方法承擔舉證責任。
[6] 究其原因,是因為新產品在方法專利申請日前不為公眾所知,經由專利方法制造的可能性較大,其制造方法的證據又處于被訴侵權人的實際控制之中,因此,應當由距離證據更近的被訴侵權人提供該證據證明針對自己的侵權指控不成立。當使用專利方法獲得的產品不屬于新產品時,意味著在方法專利申請日前,通過其他方法已經制造出同樣的產品,因此,同樣產品經由專利方法制造的可能性就沒有新產品的大,如果也適用舉證責任倒置規則,一律由被訴侵權人對其制造方法進行舉證,就有可能被專利權人濫用來套取被訴侵權人的商業秘密,不利于對被訴侵權人商業秘密的保護,所以法律和司法解釋沒有規定適用舉證責任倒置規則。
[7] http://www.gov.cn/xinwen/2015-12/03/content_5019664.htm,訪問時間2016年12月26日。
此篇文章由北京集佳知識產權代理有限公司版權所有,轉載請注明出處